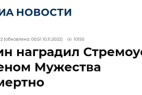“半截人”常幻痛 没有腿却总感觉刀子在割(图)
| |
| ■ 打开接受腔,彭水林痛苦地倒在床上,这次幻肢痛持续了5个小时 |
| |
| 妻子累得倒在床上。这时,她已为彭水林扇了一个小时 |
| |
| 彭水林像心理医生似的,与坠楼老太聊天 |
“半截人”的幻痛世界
◎ 文/本报记者 陈万颖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装上假肢的那一刻,“半截人”彭水林和家人开心的笑容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封面,看见消息的人都为他欢喜。但是最大的拦路虎却是自从三年前车祸以来始终没有离他而去的“幻肢痛”,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幻觉,在每一个他付出努力的关头,让他败下阵来。
7月6日,彭水林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装上了两条“腿”。在训练室,他扶着东西能走上几十分钟,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大夫们为彭水林重新站立而努力的同时,也在尝试治疗这种疼痛的幻觉。统计数据显示有70%的截肢病人存在这种现象,目前还没有方法能根治。
“半截人”苦于幻肢痛纠缠
47岁的彭水林扑倒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着。他用手挡着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似乎想把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离开。痛得厉害了,他叫喊着去抓身体下部的皮肤,软绵绵的皮肉在手掌下陷进去一大块。换了别人肯定会在床上打滚,但他不会,准确地说是不能,因为他只剩下一半的躯体。三年前的那场车祸把他拦腰截断,成了“半截人”。 那个安装着两条金属腿的树脂接受腔正静静地立在墙角,它每天只会被它的主人用上不到一个小时。
自从那场车祸后,虽然彭水林活下来了,坚强地站起来了,但当时那种痛感还残留着,已经没有的那两条腿还在不停地折磨着他。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幻觉,在每一个他付出努力的关头,让他败下阵来。
疼痛持续5个小时
7月8日上午将近十一点,47岁的彭水林推动着轮椅,来到自己的病床边。他想从轮椅上起来,却没有成功。他坐着,身子歪向左边,左胳膊肘撑在扶手上,手掌托着头。
他闭上眼睛,并且发出一阵阵低低的呻吟声。妻子周爱群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
“是头痛吗?还是怎么回事?”记者问。
“幻肢痛。”周爱群轻声说。
时间仿佛停止了。刚才还快速移动自己轮椅的彭水林像一个会呻吟的雕塑一样坐在那里,保持着左倾的姿势,长达20分钟。
他皱着眉头跟妻子说了句话。他们是湖南湘乡人,平时说的普通话也带浓重的湖南口音,连护理他们很久的医生护士都听不懂,很多时候需要儿子小彭做翻译。
妻子在病床上铺了一层不到一平方米的布垫,上面有星星点点的黄色痕迹。放好后,她绕到轮椅后面,双手从彭水林的腋下环抱。彭水林自己双手撑着轮椅扶手,两人同时用劲。“唉呀……”身体离开轮椅,侧身倒在床上的那一刻,彭水林很大声地叫出来了。
这个样子的彭水林并不像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开心。他穿着一件有破洞的白色背心,满头是汗。白色背心下面,是一个从胸部以下就开始被围住的树脂接受腔,像一个乳白色的杯子,而彭水林的身体被塞在这个杯子中,恰好塞满。
他一翻身,把自己正了过来。两手伸到腰前,解开固定接受腔的搭扣。“吧哒”一声,接受腔打开成两半,里面露出彭水林锥形的身体,缠绕着一圈圈的白色纱布。
妻子轻轻摸一下,他会舒服点
也许是听到了彭水林不停的呻吟声,对面病人的护工停下手中的活,也在看着他。这个平时爱找人聊天,被儿子笑成“对着石头都能讲半个小时”的中年女人,现在极其沉默,双眼只盯着自己的丈夫。
她把纱布一圈圈解开,用一块湿毛巾擦拭着丈夫的身体。封闭的接受腔里经常被彭水林的汗水浸湿。他又不能洗澡,每天都有妻子至少三次地替他擦拭。周爱群的手在彭水林软绵绵的皮肤上轻轻移动。“他疼时,我轻轻摸一下,他会舒服点。”
彭水林没有接受腔保护着的身体非常软,周爱群轻轻地擦着,稍微多用点力,就感觉到已经萎缩的皱巴巴的皮肤下,脏器在里面流动。在他身体的左右后侧,各有两条细细的塑料导管从体内延伸出来,里面流着黄色液体,是彭水林的“人工尿道”。右边,有一个深蓝色的帆布袋,贴在身上, 那是彭水林的肛门和排泄物收集袋。周爱群坐在丈夫旁边,左手拿着蒲扇扇风,右手不停地捏着输尿管里的气泡。“很容易堵。”她说。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后,彭水林的排泄是靠人工在身体上作出的几个口子,称为“造瘘”。“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洞,黑乎乎的,也不能贴肛门袋,很容易感染的。现在是慢慢萎缩后的样子了,护理就比较容易。”小彭说。
彭水林伸手抓过枕头,身体朝左躺着,头对着墙壁。疼痛甚至让这个中年男子开始哭泣。十二点多了,周爱群依然坐在床边给丈夫打扇,丝毫没有去买饭的意思。当儿子小彭从外面回来,她才默默地出去了。这时彭水林似乎睡着了。
他们的午饭是一份酸辣土豆丝,一份豆豉油麦菜,两碗米饭,还有一份凉皮是周爱群的。“花了十几块钱。”周爱群很想给丈夫补充点营养,但现在生活费很成问题。
周爱群和儿子坐在床边开始准备吃午饭。母子俩轮番叫彭水林吃饭,彭水林动了动,嘀咕了一句。“他说他不吃。”小彭说。周爱群笑了,伸出食指轻挠着丈夫的身体,似乎在有意地逗他起床吃饭。彭水林翻了个身,把枕头挪得更近些。“他说他要睡觉,让我妈别吵他。”小彭微笑地当翻译。
虽然没有腿,却总觉得刀子在割它
当天的疼痛持续到将近下午四点。这算好的了。刚出车祸的那一年,他经常连痛两天。这种痛很特殊,是一种幻觉。
“我总觉得大腿在痛,喏,就是截肢下面的那块地方。有刀子在剁我的腿!可是我已经没有腿了,所以是幻觉。这没办法的。”第二天,彭水林边吃中饭边向记者解释这种疼痛。这个时候的彭水林,穿着一件崭新的运动服,坐在轮椅上的时候看起来和普通人无二,唯一的差别就是上臂似乎比普通人更发达一些。
“现在他疼的时候少了点了。”彭水林描述这种旁人无法想象的病症时,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病情。“我只要不痛的时候,我身体比正常人还好。你看,我吃饭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彭水林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又夹了一大筷子油麦菜。
站立已有成效,幻痛却无计可施
比起克服心理上的幻觉,彭水林似乎更热衷于现实中的重新站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效果。
7月8日,是“半截人”彭水林借助假肢站立起来后的第二天。记者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物理运动治疗室(以下简称PT室)见到了彭水林。他装着不带下肢的接受腔,坐着轮椅,一个人在PT室里面的轨道上移动。
周末并不是彭水林的训练时间,在没有治疗大夫陪同的情况下,他不应该进入PT室。但他还是说服工作人员让他进来了。由于他没有腹肌等能够使劲的地方,只能依靠胸扩附近的两小片肌肉,因此,上臂和胸扩肌肉的作用十分重要。目前,就算装上金属假肢,他也只能在扶着东西时移动自己,而且十分消耗体力,时间不能坚持太长。
彭水林在今年3月份从长沙到北京接受治疗之前,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能够站起来。“就好像中国队和巴西队踢足球,所有人都想,中国队能踢进一个球就很牛了,谁还会想着中国队能赢啊?”21岁的儿子小彭笑着说。
从坐到站、到行走,最终心理康复,彭水林还有很多道坎要闯。接受腔是否合适,胸括肌能否控制两条假肢的平衡……最大的拦路虎,就是三年来始终没有离他而去的“幻肢痛”。
幻肢痛缘自车祸记忆
他抬头对记者说:“救救我”
2004年3月的一天,彭水林去看他同在深圳打工的弟弟。他穿过了深圳布吉镇的一条马路,来到路中间的隔离墩上。这时,从他的左侧开来一辆十轮大卡车。这条路并不宽,为了避让这辆卡车,彭水林整个人几乎贴在了隔离墩上。但他没料到,大卡车居然打了个弯,冲他直撞过来……
彭水林被拦腰撞断了,隔离墩周围都是四溅的血肉。司机弃车逃跑了,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况。路上很快开始堵车,深圳市第一现场的记者恰好在现场。他当时就拎着摄像机到现场拍摄。“这个人趴在隔离礅上,他的两条腿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它的身躯,只有一点点皮肤连着,一地碎肉,非常惨。”记者梁巍回忆。
梁巍看着摄像机的镜头,突然,这个血人开口说话了:“救我。”梁巍骇然,这样的人居然还活着。
不到半个小时,急救车把彭水林送到了深圳布吉镇医院。在那里他的肚子被消毒、缝合,保住了一条性命。
彭水林始终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撞成两截了。“他不知道自己撞成什么样了,像没事一样去叫救命,如果他知道,肯定吓都吓死了。”小彭说。
彭水林现在无法回忆起自己被车撞断时候的感觉。“我现在有时候感觉到的刀子在剁我的肉,当时可能就是那样吧!”彭水林说。对很多病人来说,现在的幻肢痛很可能来源于深埋于潜意识里的“疼痛记忆”。
护士说:“见到你爸爸千万别哭”
好在残酷的事实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上了,也许是上天眷顾,这让他安心地度过了最危险的头两个月。
和父亲同在一个食品加工厂的小彭发现父亲一夜未归,不满18岁的他脑子里开始有各种猜测:是遭抢了?还是车祸?彭水林没有手机,第二天一大早,小彭买了一堆报纸回来翻,没有爸爸的消息。到中午将近11点,接到在湖南老家的妈妈打来电话,才知道爸爸出车祸了。
到了医院,小彭第一次进病房的时候看到爸爸脑袋乌黑,盖着被子。他退出来和医生说话,当时并没发现爸爸成了“半截人”。
当他第二次再进去,看到爸爸的头已经到床的中间了,按照彭水林162厘米的身高,脚肯定顶到床尾的护栏,应该不舒服。小彭就去掀开被子。“我全身一下子软掉了……站不住。我看到我老爸就像……化学实验室的烧瓶一样,脑袋乌黑,身体肿成一个球,上面插着五六根管子。”小彭慢慢地回忆那个可怕的下午。
但小彭没有哭。进病房前,护士已经叮嘱他了,见到父亲千万不要哭。
“他当时跟做梦一样,有意识,他能认识所有人,像没事一样跟大家说话,但是现在,他完全记不起来那段日子。医生不让我们告诉他病情,怕他受不了打击。”小彭说。
随着肚子被缝合,排泄问题的解决,彭水林恢复的很快。一个月后,他已经跟家人要求要出院,回工厂上班了。彭水林觉得自己的腿老使不上劲,总想拿手去摸。周围的亲戚统一口径,告诉彭水林,“他想摸的时候,我们就一边一个,按着他的手,吓唬他说脚上打的石膏,不能摸,会感染,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你就自己去摸吧。换药、吃饭的时候把床升起来,也用桌子啊别的东西挡着视线。”
那段时候,一共六个人轮流看守着彭水林。秘密一直被保守到他的身体度过危险期。
但是这段被善意隐瞒的时间里,时常发生的腿部疼痛和麻痹的感觉,让彭水林一直认为自己的腿脚还在。
“幻肢痛”说明潜意识里无法接受事实
施红梅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心理科大夫,由她负责治疗彭水林的“幻肢痛”。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存在?”属于心理医生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施红梅问。“我能看到自己,我碰到东西也有感觉,视觉、听觉……”记者回答。“这就是原因。有些病人被善意地隐瞒病情,这段时间里,他大脑对腿部的控制功能一直还存在,这可能会造成幻肢痛难以消失。对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大脑控制功能没有成年人好,或者有意识自己的某个肢体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比较有利于幻肢痛的治疗。其实,说到底还是病人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现实。他们的潜意识并不认为现在肢体残缺的这个‘他’是‘他’。”
施红梅主要是用催眠给彭水林进行治疗,这种方法叫做“S”,指的是病人经过简单的治疗过程来创造准确的身体形象的几个步骤,这样,身体和心理、感觉信息系统就会回到正常状态。
出于为患者保密的职业道德约束,施红梅只告诉了记者一般的治疗手法。催眠患者后,要引导他们去想象原来的身体,并且想象一种“生命力量”的代名词,比如红色、绿色,然后想象这种力量进入原来的身体,再将这种力量收回来。“很玄是不是?其实就是给他心理暗示,让他能够接纳现在这个自己。”
没钱,幻肢痛治疗停止了
每周一下午本来是彭水林要来上治疗课的时间,但7月9日这天他没去,他去了假肢工厂。“上课要钱的,算了,不去了。”彭水林说。
3月18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工程研究所把彭水林一家三口接到北京,承诺免费为其制作假肢。同时,心理医生施红梅也作为医疗小组的一员加入进来,从一开始就安排了心理治疗课程。上一堂课要一个小时,60元钱。“一般一周三次,平时我交代他,在病房自己要练习着引导自己。”
“五一”之前,心理治疗初步见效。有两个星期彭水林都没有再犯幻肢痛。
停课一阵子后,幻肢痛再次袭来。但与以前动辄痛上一两天相比,现在几个小时的疼痛已经进步了不少。
“幻肢痛没有‘根治’的概念。也许半年不发病,也许某一天一件小事又触动了以前的记忆,可能又会复发。”施红梅说。
家人为“半截人”心理设防
彭水林成了别人的心理医生
7月10日,一位六旬坠楼老太被送到彭水林病房的隔壁。老太太的坠楼涉嫌自杀,保险公司不肯赔款,这让老太太精神十分抑郁。
彭水林得知后,让妻子推着他来到老太床前,彭水林聊了六七分钟,讲了他自己的经历。老太太听着,表情开始柔和起来,甚至,对着镜头开心地唱起歌来。
彭水林的主治大夫田罡觉得,彭水林的心态比很多残疾人都要好。如果他能继续努力克服幻肢痛,这将是另一个奇迹——心理康复的奇迹。而彭水林和家人很清楚,没有三年来家人的细心呵护,现在的彭水林,也许不会是在PT室大吼“没问题”、为别的病人现身说法的彭水林。“他经常在接受假肢训练的时候大喊一声:‘我要再创造一个奇迹!’他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生活,甚至去帮助别人。”儿子小彭说。
儿子有意识地
挡在父亲和镜头之间
刚刚经历完一次幻肢痛的彭水林,第二天似乎心情很好。中午,儿子推着他准备到外面的餐馆“改善生活”。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近,有一家专卖粥粉面的快餐店。他们点了四个菜,花了44元钱。
正吃着,突然一道闪光灯伴随着“喀嚓”一声快门声闪过。小彭警觉地环顾四周,其实是隔着一排座位的一位母亲站起来给两个孩子照相。“她肯定在照我们。”小彭说。原本和父亲并排坐着的他把椅子拉到桌子的侧面,试图替父亲挡着镜头。
当他确定对方只是在给孩子照相后,他才把座位拉回父亲身边。
自从彭水林遭遇车祸变成“半截人”后,妻子和儿子就成了保护他的两道屏障。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骨科大夫田罡看来,经历如此打击后的彭水林的心理状态,甚至比其他一些残疾人都要好。
儿子夸父亲三天就学会轮椅
吃完中饭,小彭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往店外走。快餐店的服务员一左一右拉开玻璃门等候。彭水林在经过他们身边时,仰起头笑着向他们道谢。走出店门,要经过一段斜坡。彭水林示意儿子放手,他在斜坡顶上停了停,突然抬起轮椅前轮,只用后面的两个大轮着地,手控制着轮子,一点点放,翘着轮椅走下斜坡。小彭一直在爸爸身后,双手前伸。一旦彭水林失去平衡摔倒,他能够马上接住。
花了将近10秒钟,彭水林自己走下了三米长的斜坡。原本在下面紧张注视着他的周爱群脸上露出笑容,走上前去拍拍丈夫的肩,用家乡话说着什么。
“我爸很牛的。我上个月15日刚到北京,病房的人就跟我说,我爸学这个轮椅,三天,三天就学会了!”小彭说。
“哪有!学了一个月!”彭水林大声纠正。周围的三四个行人一直看着他像杂技表演一样翘着轮椅下坡,听了父子俩的对话,也跟着笑出来了。
五辆公车路过都不肯载他
变成“半截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彭水林都不太敢出门。小彭一直清楚地记得,今年三月份他曾经因为连续五辆公交车拒绝搭载他爸爸妈妈而打了投诉电话,甚至一度想打官司。
那时的彭水林还不能坐,他躺在小推车上,周爱群推着他来到公车站。一连来了5趟车,都不肯停车,要么就不开门。周爱群没办法,给儿子打电话,小彭让妈妈把车牌号都记下来。到第六辆车过来,他们才终于上了车。
“我很生气,作为公交车,本身就是为公众服务,对于残疾人,更应该服务啊!我一个电话投诉到他们部门去。这是我爸爸出事以后唯一一次坐公车。他心里肯定特别难过,回到家,他一直不肯说话。”
这种状况直到彭水林来到北京,安装了接受腔,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坐起来之后,才得到改善。
赔偿款没有着落
希望能开个小店
出事之前,彭水林父子都在深圳的一家食品店打工,彭水林在小工厂里做河粉,儿子小彭则在厨房“掌勺”。“我希望能有人跟我合作开个湘菜馆。我爸爸也希望将来能自己做点小生意,就和正常人差不多了,说不定幻肢痛就好了。”小彭说。
彭水林至今没有拿到那起车祸的赔款。2005年,深圳市龙岗区法院在肇事司机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肇事方赔偿彭水林24.9万元。但由于车祸发生当时肇事司机弃车逃逸,这笔钱一直只是判决书上的数字。到今天,彭家只拿到法院拍卖那辆肇事大卡车后得来的一万八千多元钱。
来到北京马上四个月了,虽然安装、制作假肢的费用不用自己掏,但住院、心理治疗、运动治疗等等花费,都欠在彭水林的账上。虽然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已经减少了彭水林的收费,但迄今为止还是欠了医院万余元。
采访结束时,一场阵雨刚好停下。小彭走在医院的花园里,笑着说,2004年要是爸爸没出事,他们应该当年就在长沙买房了,也不会再去深圳打工了。“就当现在是养精蓄锐吧!你看,就算下过大雨,但是地面总会干的。”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