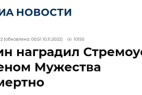上游•夜雨丨弟弟

弟 弟
杨飞
有人问我回老家耍了多久,我说两天。真按时间算,就一天,头天下午才到老家,第二天中午就回了重庆。作为教师,寒假是空闲的,又恰逢新年,无论如何也该多陪父母几天。为何又去匆匆呢?一怪弟弟犟,不听劝;当然与我怕死也有关系;另外老婆女儿也在一路,风险高、压力大。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飞沫传染、粪便传染、气溶胶传染,煞是吓人。这种病毒有些凶险,全国感染八万多人,死了两三千。二十几岁健壮小伙都战不过,有的医学专家也牺牲了。我等普通百姓,买个口罩都无门路,唯一保护措施就是远离危险之地。但是,弟弟是个危险分子,而且是一个固执的危险分子。我反复告诫:你是乡村赤脚医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待在家里,即使出门遇到的多是健康人。你每天和病人打交道,装备太差,没有防护服,就一个口罩,如果病人中有一个是新冠肺炎,你就倒霉了。他红着脸争辩说:“这个你不懂,冠状病毒早就有,新冠病毒只是一种变异。”我说:“新冠病毒类似SARS病毒,科学家还没弄清楚,世界上没有特效药,美国的瑞德西韦只是一个传说,一旦传染,全靠自身免疫能力。你是五十几的人,能战胜病毒吗?”他硬着脖子回道:“知道了,我每次看病都戴上口罩。”然后踽踽独行,消失在山坡田间,让初春的寒霜割着苍老的面颊。
他每天都出去看病,有时熬到深夜,回来一家人同桌吃饭,我惴惴不安,不敢和他对面说话,不敢和他吃同一碗菜。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回重庆安全。临行前恰好有人打电话请弟弟出诊,我赶紧劝他:“算了,你说在外地走亲戚,来不了,直接叫他送城里医院,不挣那几个渣渣钱。万一被感染,回家把爸爸和妈传染怎么办?”他回怼说:“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春季病毒活跃,生病的人多,医者仁心,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退一万步,作为医生,即使不看病,疫情期间也不能坐在家里,至少应该向乡里乡亲宣传防控知识。”我很无奈,心里着急,“你的行为确实很高尚,即使要带头也轮不上你这个残疾人,前面有干部,还有党员。你这样积极让村长、支书怎么想?你只是底层的赤脚医生,如果感染了,媒体会报道你吗?政府会歌颂你吗?假如不幸死了,能评上烈士吗?再说,聪明人绝对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我想这些无懈可击的理由即使犟牛也会回头。父亲这时也脸红脖子粗:“你跟他说不明白,他这个人油盐不进。过年那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他竟然搞到晚上九点多才回来。黑灯瞎火的,田坎路窄,藤蔓荒草,腿脚不便,摔到田里怎么办,冷都要冷死他呀!”父亲哽咽不语,嘴角抽动,雪白的胡须在颤抖,脸上皱纹比先前更加深密,抬起袖子试了试眼角。弟弟说:“你们不要说了,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知道怎么做。”然后背上药箱一垫一跛向门外走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父亲和我摇头无语。
弟弟是苦命人,本来想读书考大学,谁知遇到车祸,好不容易救回一条命,落下残疾,只有半个身子管用。考大学没了希望,打工没人要,农民也当不成,左思右想只有学个技术混口饭吃。酷夏严冬,晴天雨雾,他背个药箱,走在蜿蜒曲折的乡路上,走在荆棘丛生的山岗上,一颠一簸,在狗叫声中走进村庄,又在狗叫声中离开农舍,懂事的人叫他杨医生,顽皮的孩子叫他跛子医生。

弟弟拜了一个师傅,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擅长洗胃救人。现在的人思想解放了,吃农药寻短见的病人很少,靠这点技术难以生存。于是给他买书,我不懂医,更不知道怎么学医,只觉得多读点书肯定没错。胡乱给他买了很多书,有西医教材,也有中医教材,还有护理教材。想到农村养有牲口,又托人到畜牧兽医学院买了兽医教材,现在是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一起治。曾经问父亲:“他的医术如何?”母亲插话,“全村几个乡村医生,就他的生意最好,吊脚楼的傅草药外出打工去了,柯家庙子的六娃子没有生意,把诊所改了麻将馆。我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衣禄,你弟弟可能就是当医生的命,沟底坡上、翻山越岭的人都找他看病。”看到母亲自豪的样子,父亲解释道:“开始没人相信他,你知道村里那个周风箱,一个酒坛子、一个药罐子,气管炎严重,走路像拉风箱一样,噗呲噗呲的,六十多点就倒在床上起不了身,弄到县医院,花了好几万,医生说是肺癌,不想医了,叫他儿子准备后事。抬回家里躺在床上等死,一天到晚疼痛叫唤,家里人听得心烦,就叫你弟弟拿点药,打点镇痛针,让他死得轻松点。那时你弟弟生意差,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病人,肯定尽心尽力,死马当活马医,天天坐在他家,晚上守通宵。说来也怪,竟然医活了。”我知道周风箱这个人,五十几岁就杵根竹棒棒,听说将近八十岁才死,弟弟让他多活了十几年,也难怪村里人相信他,就是几百里外的我也找弟弟看过病。有一次吃了海鲜、西瓜,肚子拉得厉害,庆大霉素、诺氟沙星、黄连素吃了好几天,丝毫不见效果,本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弟弟打电话,他说了一种药,吃了立竿见影。
弟弟是抽过脊髓、取过头骨的人,喉头上插过管子,平时说话不多,稍有激动就口吃结巴,但这些并未影响他的智力,反倒养成了总结思考的习惯。听父亲说过,他给别人医猪,如果前边医生治疗无效,他会问用过的针药瓶甩在哪里,仔细看看针剂上的文字,从药品分析别人误诊,然后调整思路、摸清病症、对症下药。弟弟有时坚持自我,宁愿放弃现成赚钱的方法也不盲从。他给我说过,潼南有个黄儿科,名气大生意好。他曾冒充病人家属偷看他开处方,被黄儿科骂过好几回。说到最后弟弟有些气愤,“我以为黄儿科有什么秘诀,原来他龟儿子爱用激素药。”我问激素药怎么了?他说激素药确实能减缓病人症状,让病人和家属误认有效,其实激素药对小儿有害。弟弟最后还说,这种钱不能挣,黄儿科那狗日的要遭报应。有时他还搞点创新。有一年暑假回老家,村里黄石匠把腰闪了,满脸痛苦,找人背来让弟弟诊治。弟弟半边身子使不上力,怎么摆弄一百多斤的活人?我走过去想帮他一把,见他摸了摸石匠的腰,皱着眉头想了想,让人把石匠的衣服裤子脱了,只留一条裤衩。看这架势,肯定是用针灸、火罐。弟弟随后又把裤衩的橡筋剪断,用稻草给他系上,再找了一根长长的布带子绕过石匠腋窝绑上,叫几个壮劳力把石匠挂在院坝的梨树上。谁也搞不懂弟弟要干什么,针灸、火罐没必要把人吊起来,左邻右舍围着圈子看稀奇,弟弟什么东西都没带,两手空空走上去,一手抓住裤衩上的稻草,嘴里轻声叫道:“放松,放松。”突然一把扯断稻草,裤衩一下滑到脚跟,围观的姑娘少妇一声尖叫,遮着眼睛转过身去,石匠害羞的双脚一蹬,拼命扭转着赤条条的身子,听见“咔嚓”一声,好了,腰接上了。
弟弟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性子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比如这次疫情,他没有听我劝告,照常天天出去看病。我只得让父母和他分开住、分开吃,不要和他对面说话,提前作好隔离措施。但是,这次弟弟赢了,潼南感染十八人,老家的村子平安无事。也许是上天眷顾吧!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弟弟,我的心里就漾起一股苦涩甘甜的东西,直冲喉头:唉,弟弟!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