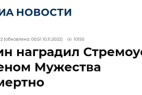中国摇滚的青春期,结束在1994年的红磡
1994年,香港红磡的一场大梦,唱不完的青春笑泪交错。2019年,高原把这个梦的碎片又拼了起来。
也许就像窦唯说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实现这些梦想的过程,就是在做一个梦。我觉得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梦里,我自己也一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
回望1994年香港红磡那场载入史册的演唱会,摄影师高原的视角和心情,与大多数人并不相同。对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人来说,’94红磡是某种精神启蒙,是渴望自由的躁动,是一路高歌的方向。
它凝聚了惊雷般的呐喊和热血奔涌的释放。它是红磡体育馆里绛红色的光雾,火焰般点燃了1994年12月17日那个难忘的冬日夜晚。
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怀念25年前那个炙热、干净、回不去的时刻,怀念那些年轻、才华横溢、毫无畏惧的脸庞和声音。
那年的窦唯是Peter Murphy的忠实信徒,西装革履,神色清冷地念着“矛盾,虚伪,贪婪,欺骗”,打铃鼓,吹笛子,超凡入圣;何勇穿着海魂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满台蹦跶,大喊“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不惮揶揄正当红的四大天王,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疑惑和愤怒;张楚安静地端坐在椅子上,眼神悲悯地唱“孤独的人都是可耻的”。
一头长发、轮廓分明的丁武有些结结巴巴地要“和香港的观众交上朋友”。邓讴歌穿着在香港买的、特意剪短的花短裤,在台上跳着、跪着疯弹吉他,年轻的大腿映满红色的灯光。
当时邓讴歌听说“香港媒体和观众看不起内地摇滚”,因此从排练到上场前都憋着劲儿,“连厕所都没上,就等着冲上台去”,最后在台上留下了一个“极度气愤并且年轻、亢奋的我”。
何勇把一瓶水淋到邓讴歌头上,再淋到自己头上。兴奋的他在《钟鼓楼》的末尾说了段话:
“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滚石公司,还有香港的商业二台,但是我最要感谢魔岩文化的张培仁和贾敏恕,他们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了许多贡献,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好吗?”
从左到右依次为:刘义军(老五)、窦唯、何勇、丁武、张楚、张炬
那个夜晚,确实有美好的演出和想象空间。一些人的青春、一个行业的愿景似乎都在里面了。那时的贾敏恕坐在转播车改成的录音间里看着台上所有的肆意张扬,签下了窦唯、何勇、张楚。
策划了唐朝乐队的张培仁则觉得此行圆满,他迎着全红磡观众的嘶吼心生骄傲,并没有料到自己后来会因为与歌手们理念不合而留下数十年的争议。
那时理想主义是主流思潮,人们单纯得几乎有些执拗。而刚刚进入内地的商业力量,还没有能力拯救仍然混乱不堪的音乐市场。
那一晚满场飞奔、忙于拍照的高原,还不清楚她按下的这无数的定格将在未来如何激荡人心。
她不知道这场演唱会会让多少男孩女孩从此爱上摇滚乐,拿起吉他组乐队,奉窦唯为神明,成为新的流行音乐偶像,在此后的每一年,追念这个属于理想和摇滚的黄金年代。
在高原看来,这不过是自己和一群搞音乐的老朋友南下香港演出而已。场面当然和过去的每一次演出一样热烈,但她并不觉得过于特别。
25年后,高原打开尘封已久的相簿,挑出百余幅从未面世的红磡演唱会照片。
2020年年初,《红磡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5周年》(下文简称《红磡1994》)一书出版。那段在岁月流逝中已然模糊的岁月,由此变得真切起来。
1
“现在看每个人的状态都太土了,就是一帮马上就要去香港的土包子”
《红磡1994》的出版,缘起于2019年年初。一卷尘封了25年的胶卷打开了高原的记忆和泪腺。
红磡演唱会之后,高原挑了一部分自己喜欢的照片印成小样留念,所有底片都交回魔岩公司,“所以我从1994年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了”。
2015年,高原将十余年间拍下的照片结集为《把青春唱完:1990—1999》(下文简称《把青春唱完》)一书时,曾问魔岩公司能不能找回当年的底片,答复是:
“台北总部地下室发大水,所有存在里面的东西都完蛋了,你的底片也可能没了。”
这份遗憾一直延续到2019年2月,魔岩唱片的牛佳伟找到高原,神秘兮兮地说:“我前几天搬家,翻出来一样东西,你肯定想不出是什么。”
高原当时大概猜到“这些可能是红磡演唱会的底片”,但当那一沓25年未见的底片拿到手中时,她还是抵不住激动的情绪,哭了。
回到家,高原把底片归好类,放到防酸底片袋中,贴上标签:“1994,红磡。”
将这些失而复得的照片结集成书,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谈及近况,高原只当这些人是朋友,而不是普通人眼中的明星甚至英雄。
她离得近,拍得到,抓住过许多不为人知又充满趣味的瞬间,这是高原从过去到现在都自信的“在场的价值”。
当所有人都仰视红磡体育馆里闪耀的明星和摇滚的未来时,高原更在意这些人的日常一面,比如《把青春唱完》里何勇赖床、窦唯踢球、一群人吃火锅的场景。
“我感兴趣的画面可能跟大家不一样,比如我对何勇在那吃盒饭这件事更感兴趣。至于他们怎么在台上耍范儿,对我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这不是我最关心的点。红磡在当时确实是一场特殊的演出,但有时候过度神化就会产生反作用,不是么?”
25年了,高原细数着这些从小玩到大、会管她叫“老头儿”的老朋友的近况:
当年何勇的键盘手、知名音乐人梁和平不幸遭遇车祸,高位截瘫;贾敏恕和张培仁近年与李宗盛一道做简单生活节,他们时常会见面;欧洋还在面孔乐队弹贝斯,有时做DJ;邓讴歌转型做制作人,为《平原上的夏洛克》《追凶者也》等电影写配乐;张楚、窦鹏、周凤岭还在做音乐,罗岩则改行拍纪录片。
谈及何勇,高原说:“他已经没办法做这件事(唱歌)了。他的经纪人张秦今年想把他过去录好的小样整理出来,出个专辑。”至于前夫窦唯,两人离婚后便没了联系。
谈及’94红磡中最喜欢的照片,高原没有选在香港街头拿着瓶装水凹造型的何勇,没有选抽着从北京带过去的金桥烟的窦唯,没有选在台上意气风发、被香港媒体围住的任何明星,当然也没有选对着镜子举起那台尼康FM2相机的自己。
她选了这张照片:参与演出的所有人背对镜头,扛着乐器、设备、行李,一行人走在深圳街头——这很像以南下务工潮为主题拍摄的某个街景,除了其中几位留长发、扎辫子的人显得有些打眼,其余人观感与普通路人无异。
“现在看每个人的状态都太土了,就是一帮马上就要去香港的土包子。”
1994年,深圳。参与’94红磡演出的歌手们拉着自己的行李、乐器和设备到火车站转车。高原表示,这是整个’94红磡系列影像里她最诊视的一张照片。/《红磡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5周年》,由高原提供
2
“我估计,现在谁都没办法让他开口说吧”
正如画家老树对高原摄影的评价——“我们在这些照片中看到了人,而不再是什么炫酷的摇滚和摄影”——高原说,“大众可能看到的都是最光鲜的、在舞台上的那种东西,但我觉得那个是假的,那是拿出来给外人看的,我不关注”。
高原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小女人,但也真实。这场演出影响了多少歌迷、如何改变中国摇滚乐进程、留下了多少遗憾,对她而言都不太重要。她只在乎记录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做什么。
“我之所以能出这两本书(《把青春唱完》《红磡1994》),其实都是这些朋友给我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最珍贵的。”
这场经典演唱会遭遇了很多意外:窦唯忘词,张楚伴奏走调,何勇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对四大天王的揶揄引来香港乐迷不满;邓讴歌“斥巨资”购买并改短的花裤子惊动了香港的检察部门,贾敏恕只能对检察人员解释“那些玩摇滚的就是这样”,才保住了这一日后被视为经典的着装……
最大的意外,在于这场演唱会的结果,诸如“中国摇滚生于1986年工体,死于1994年红磡”、“中国摇滚在那一夜非常辉煌,但也辉煌了那一夜”的评论充满遗憾的情绪。
面孔乐队的陈辉总结道:“那时的他们用音乐和态度征服了夜晚,却没给中国摇滚夜带来真正的白天。”
面对这些评价,高原觉得“他们说得没错”。这些摇滚明星并没有像现在的人想象中那样收获甚多,而是回到内地,接拼盘演出,魔岩还没有实现“让他们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的意图便黯然离场。
接下来,1994年黑豹演出荒,1995年唐朝乐队吉他手张炬车祸离世,1997年张楚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反响平平。红磡的热烈之后,是中国摇滚漫长的低迷。
何勇那句流传甚广的“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儿了”,渲染了三位时代主角和这场音乐梦最终的悲情命运。
而他的追问——“你知道张培仁在哪儿吗?这么多年了,那些用我歌的也没给我钱,彩铃什么的到处在乱用”“我就想要一个房子然后养一条狗,也不是说天天这样过。这样能花多少钱?但我这样的生活也过不上”,也成了送给那个年代和自己的、有些黑色幽默的绝响。
无论谈中国摇滚还是’94红磡,窦唯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曾说“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
与何勇一样,窦唯同样没有出现在《红磡1994》末尾的自述之中。尽管在外人看来不免遗憾,但高原的回应很直白:“我估计,现在谁都没办法让他开口说吧。”
高原觉得歌迷有时候操心太多,延展太多,脑补太多——宁可相信心中那个完美而倨傲的摇滚之子形象,也不肯相信当事人的解释。
“如果我嘴里说的他,不是他的歌迷想象的样子,歌迷就会否认,说:‘你别骗我们了,你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高原曾经和一个朋友聊天,她问朋友,为什么小窦会被推上神坛?
朋友答,窦唯这前半生不是很诗意么,特别不像我们这些俗世里的人要操心这个那个的,他被塑造出一个遗世独立、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形象,完全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这种状态是很多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人所向往的,是他们想做但做不到的,他们出于内心的投射,于是崇拜这么一个人。
1994年,香港。演出前夕,唐朝乐队在香港逛街。当时香港的一切给演出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繁华的城市生活和完善的音乐工业。/《红磡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5周年》,由高原提供
3
“理想主义,在很多年轻人出生那一天起,就没有了”
以’94红磡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若按当前音乐市场的运作规则,这批人无疑都将站在时代顶点,接受镁光灯、海量邀约和丰厚报酬的轰炸。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只是去香港演出,然后回来继续巡演,生活没有变化,甚至“达不到特别富裕的水平”。
由于当时音乐市场的商业化尚未成熟,社会与民众对摇滚明星也没有无孔不入的关注,他们的知名度和收入都没有达到预期。这更渲染了某种悲情色彩。
等到市场规范起来,这批歌手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窦唯不甘公司安排,宁愿做自己认可的小众音乐,创作《山河水》《幻听》《梦》时期的他变得“非常不摇滚”;何勇演出时说错话被封杀;张楚因为唱片成绩不佳回到西安,沉默多年。
高原近年继续拍照片,拍摄对象依然以摇滚乐队为主——面孔、盘尼西林、海龟先生、白皮书、橘子海,等等。
她喜欢盘尼西林的小乐,因为她觉得“从小乐身上能看到我们小时候那些人的样子”。高原深感现在“很多小孩只把音乐当成爱好”,而这在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白皮书主唱刘家辉白天上课写论文,晚上去school学校酒吧演出;橘子海主唱张坤明,主业是建筑师。
高原与他们聊天时总觉得诧异,“90年代就没有这样的,那时候都死心眼,我就是干这个(音乐)干到没饭吃,也会继续干。我不会想先去挣饭钱,再来养活我的爱好”。
那种专属于90年代的理想主义已然淡化了。“60后、70后,他们这个东西是在骨子里的。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主义,因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你没法要求他什么。”
至于过去的摇滚乐和现在的摇滚乐有什么不同,高原觉得摇滚其实和音乐没有关系。
“它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态度。大家都是在自己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这段时间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1994年,香港红磡的一场大梦,唱不完的青春笑泪交错。“魔岩三杰”终究没有火起来,各自回归尘世。有人无奈,有人不屑,有人坚持。没人再提出“幸福在哪里”“有没有希望”这样的问题。魔岩音乐黯然退场,张炬去世,其余人慢慢老去,按各自的步调继续前行。
2019年,高原把这个梦的碎片又拼起来了,每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不免慨然唏嘘,随之释然。
一切就像窦唯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实现这些梦想的过程,就是在做一个梦。我觉得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梦里,我自己也一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