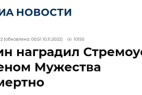30年的司法“肠梗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问题的前世今生
按: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职权并不受司法权的监督,使得公安交管部门的此等行政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恣意性,这种恣意性的结果就是导致在涉交通事故当事人在民事赔偿中权义失衡,亦影响到被控交通肇事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出罪”“入罪”。
一、缘起
某日,北京某立交桥下,遇绿灯放行情况下,某甲驾驶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某乙驾驶二轮摩托车由东往北行驶,二者均进入非机动车道,某乙车前部与某甲车尾部碰撞,二人均受伤。当日,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某乙存在车辆遇绿灯亮时,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的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某甲有驾车时有其他妨害安全行车的过错行为,负次要责任。
后,因某乙伤情变化,申请向公安交管部门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核,上级单位指令原公安交管部门重新进行认定,后公安交管部门在基本事实未变化的情况下将甲、乙的责任划分为同等责任。
某甲针对第二次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复核,被复核机关以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只能复核一次为由不予受理。同时,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当前法院不受理针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笔者感叹于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行政执法中的恣意性,认为有必要对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的历史演变进行简要梳理,以助于读者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二、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认定)之行为性质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订,下称《条例》)关于公安交管部门职责规定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第89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第91~93条)、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第108~110条),对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第94~96条)。
另,《条例》第91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在公安交管部门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般程序的行政执法实践来看,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所涉以下事实予以查明:(当事人基本情况)案涉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及所有权人、车辆保险情况;(事故经过)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事故事实;当事人违法行为和适用法律;在此基础上确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
基于上述,(1)就交通事故所涉的交通违法行为而言,不但是公安交管部门依据其享有的法定职权或职责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违法行为事实的调查、确认,而且会依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2)就交通事故所涉责任认定而言,系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确认。
故此,笔者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认定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三、关于公复字[2000]1号《公安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的评析
笔者认为,《请示》及《批复》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是否属于地方政府法制部门受理范围,涉及到《行政复议法》(1999)第6条适用的问题,属于作为复议机关的地方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判断、职权范围之内的事项。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三条规定,对于行政复议法第6条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应当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现公安部作出“地方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受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没有法律依据”之结论,显系越俎代庖。
其次,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事人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公安交管部门系行政复议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现公安部认定地方政府受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显然是既当运动员由当裁判员。
其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鉴定结论,而是具体行政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具体行政行为,前已叙及,在此不再赘述。无论是行政鉴定还是司法鉴定,均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行为。承如前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系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驾驶人、车辆所有权人、车辆保险)、交通事故违法行为、适用法律及事故原因等事实的查明,并据此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显然,相对于公安交管部门而言,对交通事故违法行为的调查及处理(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是其行使行政职权的问题,不是需要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来处的专门问题。
尽管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之前,可能出现鉴定问题,如车辆行驶速度、案涉事故车辆性能等专业问题,实践中均由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但是,公安交管部门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而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不是也不能等同于鉴定结论。毕竟,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违法行为及当事人事故责任的确认与鉴定行为的本质特征不符。
其四,事故责任认定只是起证据作用,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此,详见下述第五部分项下“其四”之内容。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不可诉
通过《通知》第四条之内容,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及公安部仅仅将事故责任认定作为一份证据来看待,并由法院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依据证据认定规则对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审查认定并据此决定是否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
五、“昙花一现”的转折——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
笔者在北大法宝上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的两起关于事故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例,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5期(总79期) 四川省泸州市中院审理的“罗伦富与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案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下称“罗伦富案”)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总73期) 福建省龙岩市中院审理的“李治芳与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案”(下称“李治芳案”)的具体案情,读者可在北大法宝中以关键词“罗伦富”“李治芳”进行检索查阅,不再赘述。但是,从两案可以厘清如下几个事实:
首先,在两案中,法院均撤销了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并责令公安交管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事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这说明,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至少在2001-2002年期间,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曾经是可诉的。
其次,法院对两起案件的受理及作出裁判,证明法院系统在2013年《通知》被废止之前,已经放弃了法院不受理关于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之定规。
其三,在“罗伦富案”中,关于公安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之行为性质,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
其四,在“罗伦富案”中,关于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审法院明确指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回到原点——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不可诉
通过具体内容来看,《法工委意见》和公安部批复内容没有区别,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作为证据使用,公安交管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以前述答复为依据作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提出的针对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不予受理,具体可见湖南省郴州中院(2011)郴行终字第45号案及贵州省安顺市中院(2016)黔04行终18号案。
七、余论
从行政法的角度上讲,公安交管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从行政诉讼法角度上讲,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无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判断。但是,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针对公安交管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经历了从“不可诉”的起点→“可诉”的转折→回到“不可诉”原点的完美循环,进而使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成为横亘于中国司法实践30年的“肠梗塞”。
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的历史发展亦可以看出中国法治的发展和进步何其不易!从目前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05〕1号文是解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但其实质不外乎对立法法第64条规定的法律询问答复之法律效力认定,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该问题。